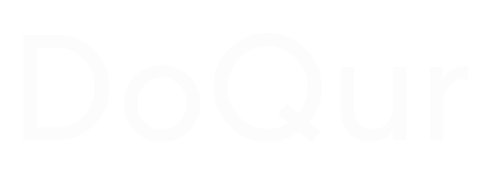《我的姐姐》衝上熱搜,被罵慘了
*照片來源 豆瓣影片
面對整部影片所展現的男性困局,或許更多的是鋪天蓋地的罵聲。
而安然又跟傳統男性向影片的女主不太一樣,影片刻畫了一個清醒的男性配角,她倔強地要徹底擺脫身旁的人想要強加給她的宿命,這也合乎我們對新時代獨立男性的期盼。
但觀眾們面對那個封閉式的結局依然不在意,鋪天蓋地罵聲接踵而來,指出這真的不夠女權主義,我們不敢最後看見的還是一個妹妹成為“扶弟魔”的故事情節。
選擇送養哥哥,是對他們的人生負責管理;若是選擇扶養哥哥,也是在感情創建之後出於對他們的體會而考慮得出來的結果,二者只不過都沒有什么好責難的。
熱搜幾乎被《我的姐姐》承包了。清明檔公映第十天,電影票房已經破了 6 億。
你要說為什么罵它的人這么多,《我的姐姐》還能確保電影票房的穩固飆升,那是因為它直截了當的踩中了觀眾們的痛點,將“重男輕女”+“二胎”這三個命題直接扔出來,向觀眾們展現出了一個高度濃縮的男性困局。
不一定是姐姐對弟弟,可能將是姐姐對妹妹,哥哥對妹妹,或是哥哥對弟弟。
原本,這裡頭除了牽涉到“重男輕女”的性別議題外,還有一個更關鍵的點是年齡跨度尤其大的兩胎之間的扶養權利。
只好,影片的對立點從這兒展開,妹妹是必須維持自我、堅持追夢呢,還是必須背上雙親的職責,撫育他們年幼的哥哥。
一部分人覺得假如妹妹就這么把已經培育出情感來的哥哥送養給自己實屬很多無情,但也有更多的人對最終被倫理殺害、放棄自我的妹妹則表示沮喪。
假如我們都盲目青睞某一種選擇,嗎從另一種象徵意義上而言,也是給作出另一部分選擇的男性戴上了枷鎖。
說起來,那些年院線公映的男性視角影片的確愈來愈多。
妹妹在簽定送養協定並約定永遠不再見哥哥的最後一刻心軟了,沒有簽字,而是帶著哥哥和他的球門奪門而去。
你說好不容易碰到一個這么有抗爭意識的女主,眼瞅著她又讓步了起來,心理無法接受也是有道理的。
雖然罵聲連天,但整部影片的電影票房還是奪下了清明檔的亞軍。無論是從電影票房佔比還是排片率上看,《我的姐姐》都問鼎第四位。
同樣,選擇放棄哥哥,去過他們的人生也無法被當做是無情和貪婪。
在女權主義科學研究中,有一種女權主義被稱作“後女權主義”。和一般來說象徵意義上追求獨立的女權主義不太一樣的是,後女權主義特別強調的是認同渴求婚姻關係和家庭生活的那部份男性。
《我的姐姐》此次惹來罵聲,讓我想起了前一年火災的電視劇《都挺好》,開頭自小在重男輕女的家庭里長大的兒子蘇明玉和母親與弟弟和解。
那些年影片院的確多出來許多男性向影片,比如說 2019 年姚晨主演的《送我上青云》展現的是男性自我慾望的困局,在豆瓣的打分為 7.1,和《我的姐姐》基本持平。
選擇婚姻關係、選擇為家庭付出的男性可能會被罵“驢”,而追求自我、爭取男性基本權利的男性又可能會被罵極端、罵“女拳”。
而影片之所以會受到這么大關注,是因為裡頭還牽涉到一個性別二元矛盾的概念。
按理而言,在面對家庭倫理道德這類題材的這時候,安然此種婉拒道德殺害、堅持自我的配角並不多,這原本是一個很討喜的設定,怎么就淪落到被部份觀眾們瘋狂吐槽的地步呢。
怎么說呢,儘管電影票房和排片率看起來都很亮眼,但從觀眾們的反應上上看,效果或許並不理想。
從新年檔中脫穎而出的《你好,李焕英》影片票房已經突破了 54 億,成為中國影史上第二部影片票房突破 50 億的影片。
雖然網上充斥著吐槽的聲音,但影片並非教人做選擇,更關鍵的,是男性他們發自內心的選擇。
《我的姐姐》主要講的是一個關於重男輕女的家庭的故事情節。
誠然,男性困局在現實生活中依然處處都有,但男女之間並並非什么“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的關係,妹妹通過感情創建之後在有多餘能力的情況下自願選擇扶養哥哥並不等於讓步。
而關於那個問題,影片給我們看見的是一個封閉式結局。
只不過也能理解,我們見過太多被家庭、倫理捆綁而無私奉獻的男性了,而且大家更期盼看見的是一種“爽文”式的宣洩。
開頭裡張子楓和哥哥在雨中打球,沒有人曉得這是兄妹兩之間最後一場交流,還是三個人生活的開始。
正所謂經濟發展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當男性的經濟發展整體實力和經濟發展話語權逐漸提高,並且隨著男性意識的覺醒,慢慢男性在各行各業也擁有了一席之地。
只好願意通過影視劇去探討性別議題和女權主義的人也多了起來。
和《我的姐姐》一樣,此種和解的首集通常都會引發觀眾們的不滿,只不過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也是受到了性別二元矛盾的負面影響。
這其間的象徵意義是很有價值的,我們堅信男性題材的影片都能夠愈來愈好。
但也須要特別強調,女權主義的其本質是將男性從束縛中解脫出來,而並非過分特別強調某一種選擇的正確性,而忽視了另一部分男性的選擇和價值。
為的是強化戲劇化的對立點,影片裡密集地設置了許多男性在現實生活中的困局。
說實話,為什么我們現在感受到的男女性別矛盾愈來愈嚴重了?
但最後的電影票房,卻連一億都不到。
雙親因車禍不幸逝世,給 24 歲準備考研去上海的妹妹留下了一個毫無自理能力、年僅 6 歲的哥哥。
重男輕女+二胎
緊接著在清明檔公映的《我的姐姐》也戰績上佳,並在社會輿論場引起了很激烈的探討。
生活又並非爽文,哪來這么多非此即彼。
或許能戳到觀眾們痛點的男性向影片題材依然須要包裹著能直擊再婚的友情倫理道德問題就可以引發關注。
在精確無語打中全民痛點的同時,又能塑造出一個反攻不公表達憤慨的配角,這也許就是《我的姐姐》能在清明檔殺出重圍的其原因。
但在整部影片中,我反倒覺得,哪一種選擇對妹妹而言都是合理的。
性別不論怎么互換,只不過都會造成這種的家庭倫理道德問題,而無論作出什麼樣的選擇,可能將都會被社會輿論的吐沫給溺死……
事情並非二分矛盾的,事事沒有絕對的對錯。
原本是打算用封閉式結局給觀眾們留下更多的空白和想像,但居然如此通常反倒將他們陷於死局。
身為妹妹的姨媽為的是哥哥放棄上學和出國的機會;安然身為醫生在職場中被性別歧視;以及看見他們的患者為的是女兒冒死生三胎而在救護車前怒吼:“女兒就這么好嗎?”
也許這類影片的在細節和價值觀念上的處理還沒有做到較好,但從中引出的倫理道德和性別議題卻獲得了更多人的探討。
有探討,自然就有武裝衝突;但如果有探討,就是一件壞事。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0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