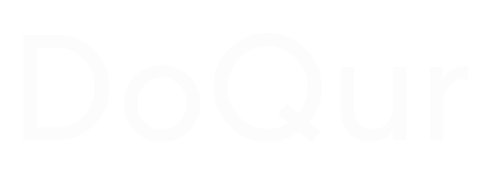《导演请指教》只聊跳蚤,不聊《寄生虫》,尬吹王一淳,嗎不妥
《音乐之声》那個小短片,講的是爸爸、媽媽和小孩生活在地下,爸爸時常到地上去搞吃的喝的,滿足一家老小的生活用度。最後,爸爸沒有從上邊回去,說是被粘住了。接著,電影來了一個小反轉,說爸爸、媽媽和小孩,都是跳蚤。接著,就沒接著了。
返回《音乐之声》那個小影片,這么一個核心感情,或許還是不錯的,是對難以活在陽光之下的現代人的一種啟蒙運動關愛。但是,一部電影經典作品好不好,原創是否,極為關鍵。王一淳拿出來的那個故事情節,在三十年前的微型短篇小說選刊類的書籍上,就已經是老生常談了。我三十年前就讀於到過相似的故事情節,講的是夫妻倆生活在地下,媽媽一直告訴女兒,地上的,都是蚜蟲,可不料,最終媽媽死掉之後,故事情節反轉,原來生活在地下的,才是蚜蟲一間。
只不過,微型短篇小說上的那個故事情節,也並非什么原創的東西。二十多年前,中國有基本微型短篇小說的選刊,當時給的稿費還挺高。我第一印象當中,那些書籍都是雙月刊,每兩本賣兩塊錢的模樣。據傳,每期都能賣幾百萬冊。這么受歡迎,稿費所以高。但是,那些報刊上邊的微型短篇小說,許多都是舶來品。當年,許多讀此類短篇小說的聽眾,都看不出外文的影片和微型短篇小說,因而,很多作者都是直接從外文內容當中扒故事情節。
王一淳《音乐之声》的問題是什么呢?是老模子還是老模子,沒有翻出新花樣來。一個陳舊無比的故事情節,更是難以將那個故事情節“中國化”,且難以賦予那個老故事情節一個新的感情文件系統,最終更是用跳蚤的攝影機去削弱故事情節的感情文件系統。此種作法,和《寄生虫》的差距,就較為明顯了。近年,有很多的影片就是捉弄部份粉絲閱讀太少,看的片子太少,總是搞此種舶來的東西。而做為影片的評論家,嗎不必須尬吹跳蚤,做什么精明人。(文/馬慶雲)
像王一淳的那個《音乐之声》,假如粉絲們觀影數目足夠多如果,也一定能在外文影片當中找出相似的。我三十年前寫到的那個微型短篇小說,只不過就是從外文影片當中扒出來的。此種又是跳蚤,又是人,又是地下,又是地上的敘事,中國傳統短篇小說的敘事當中,是不必那個路數的。此種路數,一看就是歐美的。我讀的多了,看的多了,再看王一淳的那個《音乐之声》,就覺得其缺乏原創價值。
事實上,對上邊那些老故事情節升級最好的,必須是日本的影片《寄生虫》。也是夫妻倆生活在儲藏室,也是過著見嚴禁光的生活,也是要寄生於“宿主窮人”那兒,但是,《寄生虫》最終的反轉,並非地下的人是跳蚤,是病菌,而是重新檢視窮人,檢視自己在思想維度上的問題,特別是檢視窮人、地面上的人,又是並非病菌的問題。
影片播出完畢之後,現場的來賓們大聊跳蚤。我在早前對這檔綜藝節目的點評該文當中說過,舞臺上的這群人,都是精明人。自己精明在何方了?精明在能夠為一部電影的內容做減法,但是做得肆無忌憚,甚至於有點兒沒羞沒臊。《音乐之声》那個影片,看完了之後聊跳蚤,聊小動物,都是很膚淺的,電影本身也並非說什么跳蚤的,更並非說跳蚤小孩子學音樂創作的。這片子的核心感情是:難以活在陽光下的人,自己何以生存?
12月10日早間,《导演请指教》電視節目更新了最新一期的內容。在這一期當中,王一淳編劇的《音乐之声》對戰樑龍編劇的《烙花散》。老梁的這個片子,原本是長片,非得濃縮成15兩分鐘的影片,必然故事情節講不清楚,最終失利,究竟沒什么惋惜。這一期當中,較為尷尬的,是《导演请指教》的舞臺上,我們爭相尬吹王一淳和那位編劇主演的《音乐之声》。我指出,此種尬吹不但沒有必要,但是推高了整個電視節目的質量。
但是,舞臺之上,聊那個真正的核心感情,聊著聊著,就難犯忌諱了。而且,這群精明人就懂得了怎樣給此種電影的評論家做減法了。自己這么一做減法,還在舞臺上聊得振振有詞,就十分具有後現代主義的荒謬感覺了。精明人懂得怎樣做電視節目,但不曉得怎樣為表演藝術評論家工作負責管理。即使精明,而且壓根也沒想過負責管理任。
奉俊昊的那個《寄生虫》,在創意設計上,當然有大量的歐美短篇小說和影片的影子,但是,它升級加碼了,最終成了一個有日本香味的影片,並且重新確立了有效的感情文件系統。而且,那個《寄生虫》要歐美看著,又是熟識,又是陌生的。最終,整部《寄生虫》又是戛納,又是奧斯卡金像獎的。說白了,就是歐美故事情節的老模子,翻出了日本的新花樣而已。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0 KKTM)。聯絡我們